戴上它;拿掉它;你是否受到压迫?难道你不懂这是必需戴上的?你是恐怖分子么?这是最新的潮流吗?戴著它会很热么?你为什么不戴?你为什么戴?你不会觉得羞愧?
几乎所有穆斯林女性的一生中,无可避免地无数次面对,来自穆斯林或非穆斯林的追问,关于头巾 (马来文称Hijab或Tudung)的种种问题。除去头巾可以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但是,若换了另一个情境,戴上头巾才能免除周围亲友或陌生人追问和责难的方法。
遗憾的是,戴与不戴头巾在不同族群中的讨论是非常单一的,忽视了头巾往往不只是头巾,还牵扯著国家、宗教、性别、族群、身份、空间、认同等千丝万缕的问题。唯有去理解一名女穆斯林戴与不戴头巾的理由后,我们才能不以虔诚或不虔诚的简单分类看待,让穆斯林女性在对待自身的选择上获得尊重。
太阳出版社(Matahari)上个月刚出版《头巾文选》(The Tudung Anthology),共收录了22篇的女性书写。这些女性并非全是穆斯林,来自不同种族和社会背景。有的是建筑专业的设计杂志的记者,有的是爱在家里种植蘑菇的老师,或者小学老师、前大学教授、全职母亲、医生作家、兼职或全职文字工作者等,写出她们各自与头巾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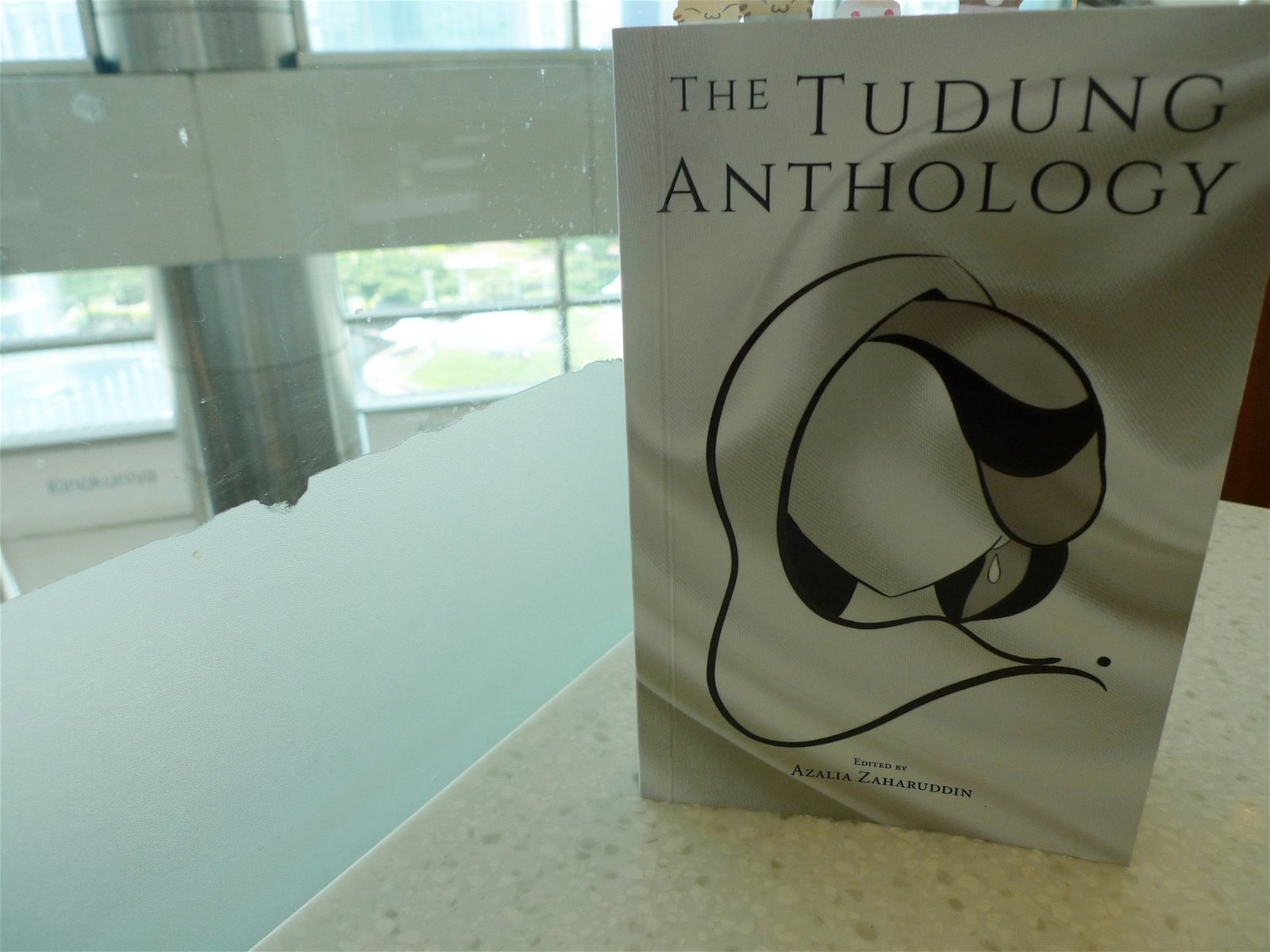
留日四年同学初拒同座
《头巾文选》编辑阿扎莉亚(Azalia Zaharuddin)原本一心想到英语系国家,修读英语或新闻专业的她,机缘巧合之下在日本香川大学,与樱花和日语相伴四年。
自小在学校习惯独处的她,从一个穆斯林为大宗的国家,只身飞到日本东北部濑户内海沿岸的一个小县市,一个语言和肤色更单一均质的社会,成为香川大学教育系唯一的马来西亚学生。戴头巾的她,比起其他留日的马来男同学更易受到旁人眼光的注目。
文化和语言的差异让原本爱发问、口齿伶俐的她,常常无法自在地参与课堂讨论。最令她难受的是,日本同学尽管礼貌亲切,但是没有任何人愿意坐在她身旁的座位。她在《家书文选》(Letters to Home)中的“Sakuras are Beautiful, but Nasi Lemak is Better”,如此写道:
“刚开课两周。他们说得对,适应陌生环境是困难的。有时候,我根本不知道sensei(日语,老师的意思)到底在说什么。看来两年的基础日语仍嫌不足,我只能呆坐在那里,看似自信地点头示意。我甚至开始习惯接受没有人愿意坐在我身旁的事实,除非那是班上剩下的唯一座位。有的人甚至宁可站在课室后端,也不愿意坐在我身边。”
受访那天,她刚好禁食,未点任何饮料。落地玻璃窗外的阳光透进书店里,天气大好,与她忆述这段回忆的内容形成强烈的对比。或许书写本身已释放她那种无奈的情绪,所以她的语气要么爽朗要么平稳,没有一丝难过。
“他们知道我跟其他人不一样,没有任何同学愿意坐在我身旁。我大受打击,开始烦恼到底要怎么办,尤其你遇到一些议题想找人讨论的时候。于是,我强迫自己要多问问题。如果我继续沉默,将不能改变什么。”
那段适应和学习成为显著少数的艰难和孤独的过程可想而知,但是她能理解这种对外国人的排外并非日本专有,况且日本社会也并非全然不友善。虽然她是该系唯一的穆斯林学生,大学还是很关注设立祈祷室的问题。
“系上偶尔有些印尼穆斯林同学,但都是短学期的学生,几个月后就会离开,只有我是四年的大学部学生。我的宿舍离学校很近,我其实可以回去宿舍祈祷就好,但是他们还是很友善,坚持要给我找个祈祷的空间。”
头巾作为标记:谁比较穆斯林?
阿扎莉亚用流利的英语,偶尔掺伴著马来语描述,提到《头巾文选》其中一篇“未竟穆斯林”(Belum Muslim)也有类似的情节。
华盛顿大学东南亚系硕士毕业的Alina Burner笔下的“未竟穆斯林”,其故事背景是发生在西方社会。主人翁安娜是一个刚信奉伊斯兰教的白人大学生,正努力学习如何当一个穆斯林,同时在祈祷以外的时间做回原来的自己。她每天花一两个小时透过Youtube视频学习戴头巾,同时学著适应旁人各种凝视;也会义正言辞地纠正想到阿富汗当兵的男性,布卡(Burqa)不是戴在头顶上的头巾,而是一种罩袍。
不谙阿拉伯语的她,拿著阿拉伯语和英语双语版的可兰经,到祈祷室进行礼拜五膜拜。几个女生从祈祷室走出来时,有个身穿天蓝色上班套装的女性站在门口,表明准备考社工执照,因此想访问一些穆斯林关于伊斯兰的议题,并直接问安娜:“我可以访问你吗?”
安娜顿感错愕,她身旁的两位工程系的朋友自出生就是穆斯林,她不过是才踏进祈祷室几次的菜鸟,却被相中为访问的对象。关键在于她们的外在装扮,决定了谁看起来比较穆斯林。安娜身穿黑袍、头戴偌大头巾;她的朋友只穿简单的运动衫和围巾,配搭牛仔裤。对方问了一连串问题,为什么男女分开祈祷、伊斯兰如何对待女性、作为穆斯林女性的经验等,安娜当下心慌地以赶时间为由,丢下两个朋友落跑。
作为穆斯林女性,基于宗教信仰,需身穿头巾和黑袍。那可以是履行宗教义务的表达方式之一,也可成为身份认同建立的来源,同时却成为西方社会的“异类”,经常需要适应和抵抗来自外在的怪异目光和偏见,严重时甚至会引起社会舆论的挞伐,或是推动落实打压少数穆斯林的政策。

责难与刺青:只是穆斯林的问题?
Raja Ummi Nadrah在“揭开面纱”(Unveiled)的故事中,提到一个在本地国际伊斯兰大学就读的女生。她每次搭巴士时,为了避开众人目光,总是习惯坐在巴士的最后一排,方便在她快到站的最后十分钟,无视巴士司机从倒后镜映射不同意的眼神,迅速地开始从书包拿出黑袍(abaya)和一公尺长的头巾利落穿上。
有次却被同站下车、不相熟的学弟,以“我是你在伊斯兰里的弟兄”为由,认为他有义务给予劝告,质问她为何不遮掩并劝她要有羞耻心,而引发两人的争论。当中不是只有如何诠释宗教的问题,还有非穆斯林一样也会面对的性别不对等的权力关系。
所以,“头巾”只是穆斯林,或穆斯林女性才会遇到的“问题”么?
不同族群社会对刺青都有一种既定观点,只是背后支撑的理据各有不同。
“刺青与头巾”,出自小学老师Shaf Ghani之笔,说的一个女人成为妻子、妈妈以后,每逢出门就会身穿全套的马来传统服装和头巾,除了是为了回避周围目光和家婆的质问,也是为了遮掩自她年轻时就已烙印在左掌附近的“Freedom” 刺青。虽然她心里不明白,为何人们认为印度手绘(henna art)是一门艺术,但是墨印刺进皮肤里的刺青就是对信仰的一种冒犯。
关于一块布的书
推介礼前两周,她开始变得非常担忧。网络上突然流传很多关于头巾的激烈辩论,她很担心人们会单看这本书名,直接判断它是一本关于宗教的书。
阿扎莉亚在介绍文中,开场就先表明立场:“这不是一本宗教书籍。无论如何,这是一本关于一块布的书籍,以及它如何能够用自己的方式编织入人们的心里,并引起各层次且不同的连锁反应。”
她表示,“我在推介礼也提到,你会明白她们戴/不戴头巾背后的故事。这不是关于容忍的问题,这跟互相理解不同,互相理解是你知道她为什么要那么做。当你理解她的理由和行为后,你才不会评价她是一个不那么穆斯林,或标准虔诚穆斯林的简单分类。”
“这些书写的女性,包括任何一个穆斯林女性,她们都在自我追寻的旅途上,需要被理解和尊重。 ”
可是,她认为当前讨论的困难在于,当有人提出疑问时,有人会在没有给予任何理由的情况下,把问题压抑下来,而难以促成真正的理解。
她今天头戴赤黑色头巾,左侧的头巾上穿过一支深粉红的大头针,简单却显眼。年纪轻轻的她,说话很有条理,补充:
“它不只是谈论头巾,也不是要讨论对错的问题,而是创造一个互相理解的空间和基础。”
她说,关于头巾的讨论,总是出现两种极端的看法:一种看法是一见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就认为她们是受到压迫、亟需被解放的女性;另一种看法则是认为,穿戴头巾是身为穆斯林女性的不可松懈的责任。

女人非“大写”:敞开心怀聆听她们的声音
在过去数个月编辑此书的过程,六十岁的母亲也一直陪伴在旁。 阿扎莉亚笑说,母亲有时也会因自己的宗教观点和立场而对文章提出批评。她语气忽然严肃起来,“这也是我希望避免的。我不希望这本书变成人们互相攻击的武器,最终使女性受到折磨。”
“我们需要敞开心怀来阅读,明白她们为什么做那样的决定。我们都可以轻易地批评别人戴/不戴头巾,但是当你阅读她们的文章时,你能够理解她们曾经经历过哪些事。”
最令阿扎莉亚感到难过的是,女性之间也会互相指责,“当女人也不帮助另一个女人解围,为另一个女人辩护不戴头巾是她的自由时,这个讨论就会变得困难。”
这说明了女人并非英文大写的女人“Woman”,内部均质单一,而是充满差异异质的小写“woman”,会受到教育程度、宗教信仰、家庭背景、社会阶级、职业类别等因素而出现分歧。
关于为何是女性书写的问题,她说,“我最基本的回答是,男性对于女性的品头论足真的已经够多了。”
“女性的身体和服装打扮经常成为男性评论的话题,例如你的裙子太短诸如此类的。我不是要批评什么,如果我们在讨论头巾的时候,还要邀请男性来跟女性说他们的看法,你会觉得......既然这是女性亲身经历的事情,就让她们说她们想说的。”
在这些女性书写中,无论是真实个人经验或是虚构的原创故事,散文或诗歌,更复杂贴实地表达了穆斯林女性在不同社会情境中的处境。她们戴/不戴头巾的原因多样,也会因为外在所引起的一连串反应,以及身在其中的各种复杂感受,影响她们在不同情况底下采取不同的回应,或顺应或抵抗。
无法将她们的态度或立场简易归类——她们是虔诚的穆斯林,或她们是受到压迫的一群,正是阅读这些文选的珍贵之处,也是阿扎莉亚不断强调出版此书的最大用意。她们与头巾之间的互动经历,是一个伴随著个人身份成长,而持续不断的漫长过程,包括各种疑惑、焦虑、愤怒、快乐和认同形成本身,端看那个社会是否允许公开开明讨论。
【请继续支持我们,推荐下载东方日报APP】
Google Play:https://odn.my/android
HUAWEI AppGallery:https://odn.my/appgalle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