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个黄昏,是在车上度过的了。上一次站在户外感受夕阳究竟是多少年前呢?我塞在车龙中时偶尔会问自己,然后试著努力回想,仿彿是洪荒时代的诗,记忆很难从里头搜索出一些线索,皱褶著的总是百无聊赖的日复一日。
这不应该是一种控诉,但生活的节奏随著年龄与身份的转变,总是比光速还快,我们适应的到底是生活还是自己?到底是从生活中适应自己;还是让自己适应生活?我没有答案,只知道每一次的适应,其实也是一次的流失。好比说黄昏,它虽然还是定时出现,但我的肌肤肉身却总是与它隔绝。
钢骨水泥大楼,车来车往的大道均将我与它隔绝,但我实在不能将它们列为主因,那是我在生活上的选择,种因得果,如此说来我就忽然变是像是个不得志的少年,总是为细微的格格不入寻找借口。
少年时光。我最后一次站在青葱郁郁树林底下接触夕阳或许便是在曾经的少年时光里。那时老家的大路还很小,大龙沟也不大,草场公园还是傍晚时分男女聚会的首选。那时我几乎每天穿著球鞋球衣,怒喊嬉笑狂奔呼吼,让皮球滚动直到最后一丝阳光隐没,才愿意归去。彼时只要脱开上衣,夕阳的吻痕清晰可见,烙印在有致的身线上。
如今他们说我皮肤白皙,西装皮带皮鞋,笔挺地走在公司间看不出往日是个驰骋草场的追风少年,这都是坐在冷气办公室内的恩赐。我往往陪笑,但清楚知道已经松弛肥大的肉身,那是个没有受到夕阳祝福的臃肿,在镜子前一览无遗地展示著对过往的放弃。
有人说这是进步,我们总不能困在某个时光里出不来,而衣著打扮越发鲜丽,身形越发走形,便越能证明在社会上占得一席之地,真的是如此吗?
红灯亮起,我生命中的90秒就这样被偷走了。曾经从蒋勋的书上读过他以味觉对人生进行剖析。甜酸咸辣苦,到底我现在处于哪个味觉境况呢?如以年龄分,中年的我已过了甜酸之境,迈入咸辣的阶段,而苦也悄悄探头,不时流出。但我们其实无法任由某个味觉在某个年龄层时主宰,或许孩童时少年时还可以任甜味甚至是酸味弥漫全身,然而一旦步入社会以后,五味杂陈才会是主旋律,即使我们奋力抵抗,期望按部就班,让甜味维持得久一些,让苦味迟一些才报到,但总是徒劳无功,改变不了的事物,慢慢就成了我们适应得了的事物。
绿灯亮了,车子走不到十分钟,就在同样的大道,同样的时段,同样的高楼,碰见同样冗长的车龙。会不会其实我每天这个时段都在和某一个人甚至是某一群人一起过,想想好像还挺浪漫。然而,读过JulioCortazar的小说《南方高速公路》的人会知道这种城市脉搏其实是一种荒谬。一场塞车将毫无联系的人捆绑在一起,偶有交集,做了一些平日不会做的奇事,但最后终归要回到彼此原来的生活中,当个齿轮,继续轮转。
但城内人已经习惯了这种塞车的日子,当他们选择来到城里工作与生活时,便已经默默接受了这种模式,没有对错,只有承担或者逃脱。
我说的其实是我自己。我可以用《南方高速公路》里“却没有人真正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匆忙,为什么要在夜间公路上置身于陌生的车辆之中,彼此间一无所知,所有人都直直地目视前方,惟有前方”——这一句话来诉说自己的愤世嫉俗或者看破红尘,然而将自己投入到这种荒谬的生活的,也正是我自己。
我就这样选择了在车龙中缓缓前行,也选择了在这样的环境里偶尔偷取月光写诗,本来以为可以当作一生的志业,现在必须靠熬夜来达成,而白天的自己和夜晚的自己,已然是两个面貌。
我曾在另一篇散文中写道:熬夜是现实的解药。本以为如今可以将此想法改变甚至颠覆,无奈反而成了诅咒,惟有在深夜伏案时,才能想像夕阳,写作夕阳——正如我现在写下这篇文章时,月光已经打在窗户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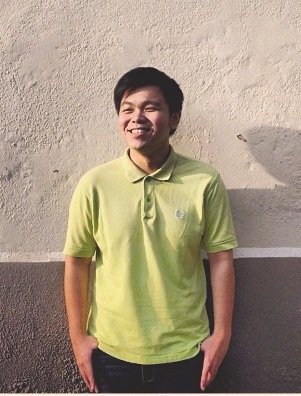
【请继续支持我们,推荐下载东方日报APP】
Google Play:https://odn.my/android
HUAWEI AppGallery:https://odn.my/appgallery

